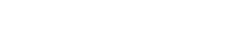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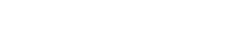
延安时期被公认的“榜首美人”长相非常娟秀49年被逼来到台湾
1937年冬,北京法源寺外的梧桐叶被北风卷得簌簌直响,吴光惠抱着几本英文原版教材,箭步穿过深巷——这一幕后来被她称作愿望的起点。
她1914年生,父亲任职国民政府财务系统,注重新式教育。教会学校、上海商学院、北京大学,是同龄姑娘难以企及的肄业轨道。
讲堂之外,街头的抗日标语更能点着她的血性。“国家兴亡,责无旁贷!”每当听到这八个字,她的眼睛亮得像火把,那时她不过十九岁。
一次英语演讲比赛,她和北大学生张砚田邂逅。两人谈抱负、谈救国,很快进入婚姻。世人送来一句话——携手报国。但是两年后,方向呈现裂纹。
1936年末,张砚田远赴日本留学;吴光惠留在国内,做教师、跑剧社、翻译稿件,岗位频换,是在寻觅真实能投身的舞台。一二九运动迸发后,她更难本分。
1938年5月,两人齐赴西安为杨虎城效能。权利的漩涡让张砚田心神不定,她看得理解却无意同流。“路不同,各自安好。”非常钟办好离婚手续。

同年秋,经救国会友人举荐,她坐货车闯进延安。中心急缺外语主干,周恩来决定:由吴光惠担任外事翻译。
延安缺粮缺布,却不缺热心。清晨,她抱文件奔枣园;陪英国记者雪地漫步,她跟在身侧做口译。有人低声感叹:“这姑娘,可算我们的榜首美人。”
半年使命完毕,她被派回西安埋伏。军统很快发觉端倪,出人意料的逮捕以张砚田的个人担保换来暂时自在,但全天监督并未停止。
1940年末,两人复婚,更多是权宜之计。她私自与党组织保持联系,三度恳求回延安,皆因交通和安全被婉拒。
1949年11月27日,重庆夜空炮火没有散尽,机场跑道灯闪成一条灼亮长线。张砚田拽着她冲向舱口,她挣扎刹那,低声说:“我不想走。”终究仍被推上军机。
飞机跳过嘉陵江,她透过舷窗望向暗淡河面,那片土地的灯光刹那消失。她没有掉泪,神态出奇地安静。
抵台后,她被组织在外事部分收拾案牍,笔迹自始自终整齐,却再无早年热情。夜深,她总翻出在延安的小相片,轻语一句:“总会回去的。”随即把相片折好藏回夹层。

岛内空气炽热,白天时间短。三年曩昔,她姓名进入黑名单——“与共党有染”。她挑选缄默沉静,在低沉中保存那段赤色回忆。
多年后,有人问她是否懊悔离去,她仅仅淡淡一笑,轻吐两字:未曾。外界再难追踪她的行迹,可在广阔海峡彼岸,一直有人记住“延安榜首美人”的故事。
吴光惠的人生跨过民国、新中国与海峡两岸。她在延安逗留仅半年,却以那半年的火光照亮尔后年月;命运未能让她重返黄土高坡,却留下了娟秀身影与据守信仰的传说。
